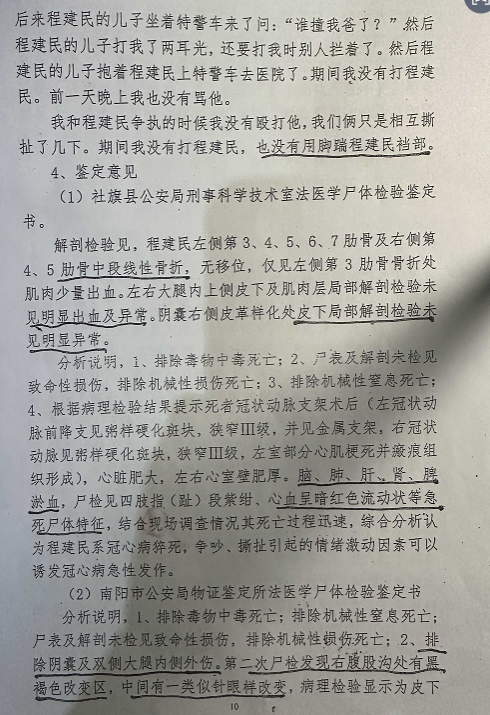|
你的心灵是否曾经遇到过与以下难题类似的问题? 如果因为贫穷,我穿上了母亲为我偷来的大衣,我是否会成为罪人?母亲源自真爱的行为,是否可以被定义为罪恶? 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时,心柔软得都要碎了,然而当我们目睹成千上万个饱受饥饿煎熬的儿童时,又变得刀枪不入起来?
节选: 内疚与羞耻 “羞耻感是所有暴力最主要或最终的起因。”缺乏内疚是社会病态的显著标志。 我是从一部伤感的B级影片知道内疚的。那是我妹妹挚爱的电影,叫做《暴雨狂云》,女主角是一个德国女孩,被驻扎在阿尔卑斯小镇的四个美国士兵强暴了。可以说,这个可怜女孩唯一的罪过便是她的美丽。但在影片里,人们把她当作娼妓肆意嘲笑辱骂,毫不尊重。在审判中,由威廉•荷顿(William Holden)扮演的辩护律师为伦理的胡桃夹子所禁锢,不得不为这些恶棍们辩护。是毁掉证人席上那个无辜的女孩,保护这些无赖的士兵,还是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他在这些抉择面前左右为难迷惘。当看到无辜受害者被厌恶女性的小镇暴徒认定为有罪时,真的让人十分心痛。 对于我来说,《暴雨狂云》是另一件伦理的“蓝色外套”之谜,不禁使我联想起少年时代的谜题。人们可以很容易看到事情的两面,但是你会发现内疚与羞耻会轻易被个人选择的角度所重新排列、过分夸大或贬损缩减。本身无辜的女孩看起来像是满怀罪恶,而美国大兵则成为了日耳曼妓女的受害者。这个故事与我们家的悲剧有相似之处。我母亲是一位已婚男人的情妇,这在附近的街区已经众人皆知了。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社区人们羞辱和评头论足的对象。虽然我知道,除了恶劣的坏名声以外,我们并不是坏人。像威廉•荷顿所饰演的聪明律师可以轻易处理这种状况。但是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又在哪里?我对公正感(perceived justice)那狡猾灵活的本性感到困惑不解。似乎在伦理的拼图系统中,羞耻和内疚是可以移动的板块。羞耻是由外部给予的伤害,而内疚则是人们对着自己挥舞的一条鞭子。只有当他人注意到我们所犯的错误时,羞耻感才会油然而生。然而当我们心怀愧疚,会倾向于闷在心里,保持一种私密性,那种感觉好似犯错之后的懊悔,或者当其他人认定我们是犯错的一方。负疚感会引起赎罪和弥补,实现积极的道德目标,而羞耻感则只会使人们在预期社交被拒绝的过程中,建立起防御机制。事实上,卡罗尔•吉利根的丈夫,精神科医生詹姆斯•吉利根认为:“羞耻感是所有暴力最主要或最终的起因。” 内疚意味着对不当的行为,改过迁善即可;而羞耻则意味着一个人自身犯了错误,并且没有办法去消除这种感觉。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偷东西而心怀愧疚,但却因为做贼而满心羞耻。我们可以从AIG(美国国际集团)丑闻爆发后的状况印证这一点。虽然通过其他手段难以追回资金,但是当公众对政府纾困公司的众多董事所领取的过高奖金发出强烈抗议时,有75%的接受者归还了奖金。我们为自己成为一个坏人而倍感羞耻,因为做了坏事而满怀内疚。在面对女性时,男士可能会因为贫穷、秃顶或扁平足而羞愧不已。但是只有伍迪•艾伦(Woody Allen)才会感到内疚——他对任何事都感到惭愧。当我们觉得自己违反法规时,愧疚感会油然而生——会有警察破门而入,狠命踢我们的屁股,而内疚的程度则“与受害者所感知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成正比”,哲学家理查德•乔伊斯(Richard Joyce)这么说。 内疚在社会规则系统内部发挥作用。在了解到是什么引起他人的不快或反对后,我们会相应地修正自己的行为,使其不仅与规则相符,还与规则背后的信念保持和谐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不管会不会被捉住,都对社会违法行为深感愧疚的原因。对我们而言,这种一致性使生活更加轻松便宜。做决定时,我们无须再重构道德齿轮,只要接受内在罗盘的指引即可,包括内疚在内的惩戒方向可以培养合作行为。当社会规则公平、公正时,保持这种一致性当然是好事,但是当不公正及邪恶占据上风,大肆盛行时,我们将不得不在愚忠顺从和诚实正直之间做出抉择。正如弗朗斯•德瓦尔提示我们的,天性已然将“像脸红这样的故障安全防护装置”根植于人类体内,使得内疚可以被轻易地察觉探测。这也是为什么违反和抗命如此不易的原因。“脸红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它意味着在某个时间点,我们的祖先开始在诚信中比机会主义中获益更多。”德瓦尔解释道。这种预警系统增强了我们的犯罪感。缺乏内疚是社会病态的显著标志。反社会人士不仅对于其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不屑一顾,而且还会明确告诉你,他们根本就不会脸红。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